第一次购买“虚拟恋人”的“包天”服务,毛昕然(化名)体会到恋爱的感觉。这项兴起于2014年的付费服务,提供陪聊、哄睡、逗笑和一切给人以“恋爱”氛围的陪伴,作为店员的“恋人”们被包装成一个个商品,吸引着在当代生活中感到孤独疏离的人们投身网络世界,找寻新的连接。(3月30日澎湃新闻)
在美国电影《Her》中,一位中年离异宅男爱上由代码生成的小姐,温柔体贴又幽默风趣,在需要时出现,从不无理取闹。直到某天,宅男发现“她”同时和8316人联系,并与其中641人相恋。如今在网上走红的“虚拟恋人”提供的就是这类情感体验服务,只不过“虚拟女友”是活生生的人,与人工智能女友还是有明显差别。至于一些男青年找的所谓“萝莉”“御姐”“女神”会否是“抠脚大汉”,一些女青年找的“暖男”会否是“悍女”,则很难说。
有需求就会有供给。花钱找个“虚拟恋人”谈场恋爱,一可缓解一些年轻人的单身焦虑——来自自己年纪越来越大、对象越来越没着落的焦虑,来自长辈催婚的焦虑;二者,在恋爱、结婚经济成本太高之下,可以缓解一些年轻人的紧迫感、窘迫感——谈个“虚拟恋人”不用担心难以支撑恋人过上优渥的生活;三者,在现实社交越来越少、社交恐惧越来越严重之下,“虚拟恋人”可以陪伴自己,为自己排忧解难。
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“虚拟恋人”可以全面走红,值得成为无数青年男女的社交替代者。“虚拟恋人”将网恋从无偿随缘式的网络偶遇,变成有偿的线上情感交易,可能诱发多种风险。一是易模糊虚拟与现实的界限,贪恋“虚拟温柔乡”,对“虚拟恋人”产生严重依赖,更不愿在现实中恋爱,更找不到现实的恋爱对象;二是过度沉迷于“虚拟恋人”的甜言蜜语,容易上当受骗。据报道,一些不法分子在社交平台伪装成“高富帅”“白富美”,制造“杀猪盘”,等待急需情感慰藉的受害者上钩,导致受害者财产损失;三是部分“虚拟恋人”可接“污单”——以文字、语音等进行性挑逗,甚至会提供打“擦边球”的色情服务,危害年轻人。
可见,“虚拟恋人”虽可以有,但不能放任,网络平台的监管要跟上。比如,加强对这类情感、心理服务的资质、真实经营情况的审查核实,即是把好入门关;对平台上打着“虚拟恋人”幌子进行欺诈、色情服务的店铺,平台负有法定监管、清理义务,不能为流量或短期效益视而不见。相关部门也要加强治理力度,对于平台纵容涉欺诈、涉色情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,应予以坚决打击并向社会通报,对于处在监管真空的“虚拟恋人”等新业态,也需要及时建章立制。
而高校、妇联、共青团、工会等应引导单身男女,看清消费者和“虚拟恋人”的关系,是短期性的商业关系和金钱关系,而非情感关系,让他们明白,追求爱情是人的天性,但不可寄全部希望于虚拟世界,虚拟世界带来的快感,终究只会转瞬即逝。正如《Her》里,代码小姐最终只能伤感地告别,从此便在云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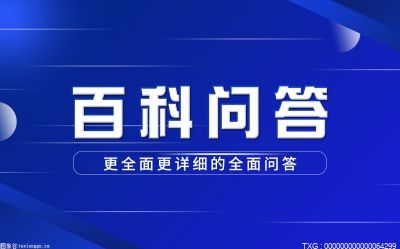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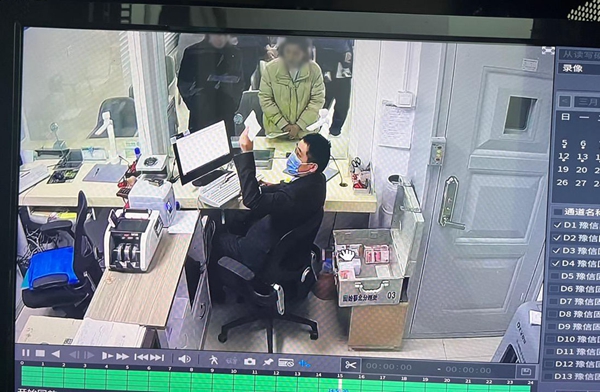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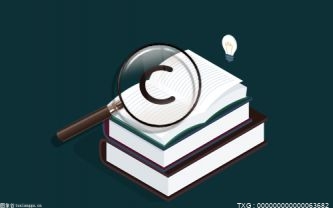




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